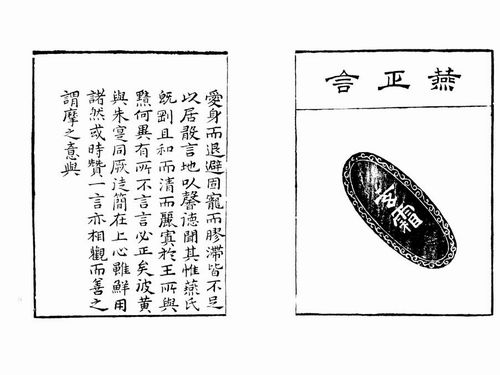行願大千
——記當代宗門耆宿上印下空長老尼
文/頓宇
【作者按】一日,跟明堯老師談起家師的開示,老師遂要求學人寫一篇介紹家師的文章,並說:“很久就想有一篇介紹長老的文章,希望通過你的記述,讓更多人了解這位住世的中華第一長老尼。”被老師這麼一說,學人便覺得任務重大。但家師近百年的傳奇身世與不凡行履實在不是輕易能寫就,何況無數的寶貴開示和日常接機?要把這些濃縮於一篇文章,煞是困難。但另一方面,學人亦和明堯老師有同樣的願望。於是只好硬著頭皮,毅然承擔下這個任務。家師平日以“應無所住”為行持,以“行願大千”為大用,大金山每年舉辦的女子禅修夏令營,都以“應無所住,行願大千”為宗旨,故本文擬以“行願大千”為題,願讀者能透過粗淺的文字,薦取吾師之心爾。

上印下空長老尼德相
恩師上印下空長老尼,字了源,一九二一年出生於江西臨川,出身書香門第兼中醫世家。生逢亂世,年未及笈便遭國破家亡,師遂頓悟世幻,捨塵出家,當時年僅十九。翌年,師便手興金山,將一處茅棚建成莊嚴殿堂。不久,又創辦中醫傳習所。
新中國成立後,環境改變,師深達時務,即創辦尼眾織布廠,工禅並重,被省政府作為模范宣傳。一九五五年,師往雲居,得虛雲老和尚指點而具戒。時虛老眼見此小沙彌尼,便摩頂道:“普度眾生,普度眾生。”在老人指點下,師南下廣東投奔本煥上人。之後在廣東一住三十年,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。在那個“史無前例”的時代,出家人頗難自保,很多僧尼還俗。吾師晝以“應無所住而生其心”兢兢勞作,逆來順受,夜則長坐參禅。
改革開放,本煥上人昭雪出獄,師秉命輔佐上人復興丹霞別傳寺,任知客。一時,“男眾道場女知客”,林下稱奇。
一九八五年,在臨川政府三請下,師重回故土,再度復興金山。鄉人猶記得這位奇女子。聞師歸來,競相擁護。師亦喜獲頓成、衍藥等得力弟子。師傾其心血,苦心經營,德感人天。山寺開光之日,天放異彩,有一巨大光環籠罩金山上空,有信眾見觀音菩薩現身,一時間,“觀音菩薩為金山寺開光助興”成為盛談。而四方衲子亦慕名而來,師遂開堂接眾。然是時,佛教元氣未復,教內凋零,僧才空前冷落,而女眾僧才,更是寥寥。為改變這一局面,師再發宏願,決定創辦佛學院。師辦學院,除因紹隆僧種,更是前瞻性的看到發展女眾教育既是佛教的需要,也是社會大勢所趨。之後,事實證明了這一理念。迄今為止,“江西省尼眾佛學院”已經送出上千名學子,於各地弘法或者深造。另一方面,作為禅宗道場,不可能離開坐禅,但當時國內寺廟,有禅堂的並不多,女眾禅堂,更是沒有。師又挺身,再一次“無中生有”,建禅堂,立規矩。如今,女眾自掛鐘板的禅堂,唯金山耳。自從有了禅堂,金山寺亦和其他男眾禅宗道場一樣,每年舉行“冬季禅七”。
接觸過禅宗的道友都知道,打禅七是禅宗用功上的一個重要途徑,旨在克期取證。一入堂即告生死假,高掛缽囊,萬緣放下;都攝六根,以悟為期。咬住一句話頭,一路逼拶,九個七下來自有受用。但其間必要有明眼師匠護持把關。因參禅一途,直捷但險峻,若無明眼人提持,稍有不慎,確是十人九蹉路。是以師父每次必親任主七,不管多忙都要抽時間進堂開示,為這些用功的禅和打警策。而很多人都覺得只要有老和尚在,就很踏實。甚至年年有幾位師父從香港、台灣特地趕來參加金山禅七。師父經常在禅七間告誡我們一定要趁年輕趕快努力辦道,老了想用功色身都不配合就晚了,她常說:“你們比我有福報,能進堂打禅七,要好好參,若人靜坐一須臾,勝造恆沙七寶塔;寶塔終歸化為無,一念靜心成正覺。既進得禅堂來就和這一法有莫大的因緣,就要好好在這一法上用功得受用,我老了,希望你們比我先成佛。”一位參加過十多屆禅七的師父曾經對我說:“真的很感激老和尚給我們撐起這一片天。為了這支靜香,有太多人在付出。”
除了打禅七,師父亦把“坐禅”納入佛學院課程,使“江西尼眾佛學院”成為一個獨具禅宗特色的佛學院。而數年後,因山上發展受限,師又在山下另建“大金山寺”,此名為本老所賜,取義為“地方大,人才大,發心大”。不久,宜春政府亦請師出山,復興末山尼祖庭。佛門有句話“馬祖建道場,百丈立清規”。而後代祖師們也大都不遺余力的建道場,今吾師亦“步其後塵”,這到底為何?難道非此不足以顯示他們的能耐神通麼?但不管是贊歎也好,疑問也好,師父只是深深地說了一句:“女人太苦了!女人求道太難太難了!”這無不是師父在磨難中走來的切身體會。當年求學無門。為了想去禅堂,甚至被遷單……但即便如此,吾師仍然不改初心,在大風大浪中捨身保存這一領袈裟,本色依然。其中的曲折艱辛,豈是我輩能夠想見的。自己受苦,故願他人離苦,願同為女性的出家人有一個安心修行的地方,願那些世間更苦的女性,有一個可以回的家……但這最終亦不過示現而已。菩薩度世,果有什麼理由呢?
師為法忘軀,而對於社會,同樣展現了一雨普潤的悲心。辦慈善基金會,支援災區,扶持貧困。不但捨財捨物,更讓世人體會到什麼叫“無緣大慈,同體大悲”。師父總是願意親自去看望那些與她素不相識的人們。有一次她老人家摸著一個孤兒的頭說:“仔啊仔啊,你掐了好多苦!”孩子溫暖得如同回到了母親身邊。
師下及小、上及老,目睹僧眾年老孤苦,年輕出家人父母無依,更憂傷廣大信眾、社會老人缺乏臨終關懷。於是不顧自己年逾九十,又著手建起了占地三百畝的安養院及慈善醫院。以使“老有所養,老有所歸”……但與此“矛盾”的是,她老人家自己卻連一個獨立的方丈院都不享受,至今還擠在一間不太通風的小屋裡。
師父的無上德行得到教內教外的崇敬,海內外的很多尼眾都渴望得到師父的傳戒。而不管戒場有多遠,師父都從未拒絕過,親任尼和尚。至今,她老人家所授的戒子已達三千余名。而師父的社會頭銜更是多得自己都記不住。但這些對於她老人家來說,不過夢中佛事罷了。
師尊建法幢於處處,更是破疑網於重重,對我們這些徒眾隨機施教,解粘去縛。以本分接人,從不弄玄虛,同時又絕不拿佛法作人情,不跟你客套,不容你鑽空子。只是學人福報淺薄,並無很多機會承教師前,加之根器平凡、出家日短,對於師父的很多教法並不能一時領會。以下所述的幾則師尊接機片段,確是“以蠡測海”;但若有人以此見海,則幸甚矣。

上印下空長老尼德相
其一 臨濟家風
恩師作為臨濟宗第四十五代傳人,得法於本煥上人,上人為師賜偈曰:“常培無量諸福慧,真如法性永長存,印理明心廣度眾,空了一切化大千”。師尊秉承家風,於當機處,毫不手軟,痛下鉗錘。一次,正副監院因寺務勞累,都沒上殿(師父直到九十歲還堅持每天上早晚課),師父發現後,便遣侍者去叫。二師情知不妙,下殿後立馬往丈室認錯,剛到門口,師父劈頭就罵:“我都上殿,你們竟敢不上殿,我打死你們!”
一次,師父來山上跟我們一起過堂,齋畢講開示,師父先轉頭看看東單,又轉頭看看西單,然後問:“xx怎麼沒來過堂?”僧值回答道:“xx師父這幾天一直在忙xx事,很辛苦,所以沒來過堂。”師父於是大罵:“出家了,死都不怕,還怕辛苦!趕緊把她給我叫來!”我們都很詫異,師父並不經常上山,卻能在目光一掃之下,就知道誰沒來。
跟在師父身邊的侍者們更是以挨罵為家常便飯,罵要挨,事還要做。一次師父很晚回來,洗完澡換了衣服就回房間了。侍者早就等得眼皮打架,師父剛走,就立馬撲向枕頭。但不到兩分鐘就聽見師父敲門:“衣服洗了嗎?”“師父,我明天洗。”“拿來我自己洗!”侍者還想耍賴:“師父,都這麼晚了,明天再洗吧。您又不急著穿……”“明天死了呢!”被這一喝,侍者一下子不困了,抱著衣服沖向洗衣房。後來她說,從那以後,她當天的事情基本不會拖到第二天。誰敢保證明天不死呢?
一僧入丈室請假,原因是參加女兒婚禮,師父問:“你受戒沒有?”答曰:“還沒呢,師父。”“那趕緊還俗!”嚇得伊再不敢思想俗事。
某執事:“老和尚好厲害啊!昨天開會,我正在想跑,忽然聽見老和尚一聲大喝‘打什麼妄想!’嚇得我一抖,再不敢跑了。”
曾有親近居士向師父告假,說是想去別處過年,師父當著很多人的面罵道:“一個寡婦,瘋跑什麼!”臊得那居士現在還記得這話,之後一直跟在師父身邊,終於出家。
師父罵人並非情緒發洩,更不是脾氣暴躁,而是慈悲到極點。被她罵過的人都深深受益,以至每有人挨罵回來,就說:“又被老和尚加持了。”
其二 隨方解縛
中秋,眾人圍在師父身邊賞月,一僧拿著一精美信箋走來,說:“師公,我作了一首詠月詩,請您批評一下。”眾人亦湊趣道:“念出來我們也欣賞一下”。那僧笑瞇瞇的正要念,師父冷冷來一句:“我不聽。”接著又說:“除非你是求我印證。”僧尴尬無語。事實上,偷心不死,貢高我慢,情見深重,是很多出家文人的通病;師父如此,正是於痛處扎針。但師父自己卻作得一手好詩,寫得一手好字,只是平時從不顯露,偶有需要,則一揮而就,就像時常在練一樣。真是“但得本,何愁末”。
同樣一次,我彈琴給師父聽,也碰了一鼻子灰。雖然在座都交口稱贊,但師父半個好字都沒說,而是要我把琴“放下”。於是某甲當即把琴從陽台扔了出去。以這一“豪舉”來表示跟琴一刀兩段的決心。之後確實再沒彈過。後來有一陣子,法堂的廣播忽然放起《普庵咒》(一首古琴曲),蓦然一聽,心不由顫了一下。而那段時間成天就放這個。對於一個曾經嗜琴如命,指不離弦的人來說,真是一種煎熬。某一天正在這種難過中打拼,偶見一句“見聞如幻翳,知覺是眾生”,言下忽得清涼。吾人曠劫在聲色幻塵中過活,認假作真。而畢竟這音聲從何而起?畢竟又是誰在聽,誰在動心?這動的心畢竟又在哪裡?帶著這種追索,之後每天故意聽這首曲子,直聽得漠不關己。後來有一次,師父饒有興致地跟我聊一位琴藝高超的比丘尼,我隨之贊歎而已。師遂放過。
一僧哀告師父:“師公,我好煩惱啊。”師父便問她:“你的煩惱在哪啊?拿出來看看。”這僧當時一懵,憨態可掬,惹得我們大家都笑了。師父又告訴她:“別人罵你,你就當作在誇你嘛。”接著師父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:“有夫妻倆,男的脾氣特別好,但女的還是經常罵他。有一次,女的又在不停地罵,男的把飯菜做好後,手裡拿張紙,拿支筆,就去叫她:‘你先吃完飯再接著罵吧,如果怕忘記罵到哪了,就記在上面……”聽得我們哈哈大笑,師父也笑。終於,那僧心開意解地回去了。後來得知,她那天真是和人吵架了。
有位飯頭因為天氣潮濕米裡使勁生蟲而愁得要命,因為出家人是萬不可殺生的,但那麼多的蟲子,要挑干淨幾乎不可能,於是她每天都很郁悶,感覺自己欠了很多命債。有一次碰見師父,就把自己的苦衷道了出來,沒想到師父說:“那些蟲子吃我們的米,我們就吃它!”僧疑惑而去,但終於不那麼糾結了。宗門下接人,無非隨方解縛,不讓人認死理。學人執在哪裡,就在哪裡施展。比如著名的“南泉斬貓”,斬的亦無非當人的情見執著。但有人因此誤以為宗門輕忽戒律,不知這些手段不過具眼師匠的方便而已。事實上,很多宗師持戒都特別精嚴,只不過,在宗門下,“戒定慧”並不是一個次第的過程,而是“等持”的關系,非是離開當下的般若觀照而去持死戒。
一僧請益:“師父,我不會做功夫,請您慈悲開示弟子怎樣做功夫。”師父道:“做什麼功夫!我這麼大歲數還不會做功夫,做事!”其實,“我要做功夫”已經是妄想馳求了,離開當下的一念心,哪裡去找功夫來做呢?
其三 向上直指
一次,學人向師父請求行三天“般舟”,師父不同意,說:“修行是要借假修真,不要把身體搞垮了。”但我執意說:“師父,我曾經行過,我吃得消。”師父便開示道:“禅宗是最高尚的,我們要在心地上用功,要在日常上用功,你在做事,那你看看這個做事的人是誰?你在生氣,那你看看生氣的這個人是誰?《金剛經》講無我相,無四相,我們就是放不下這個我,放不下你就看著嘛。平時要多誦《金剛經》,慢慢就明白了。”聽師父一說,我才醒悟到自己又心急了,向外馳求,妄想通過極端的方法快速開悟。同時還是潛意識裡認為修行就要吃苦。對我宗門的“省力”還是沒有真正承當,若非在師父這樣的明眼人身邊,早已入歧途矣。
師父平時會經常問:“你是哪個啊?哪裡人啊?”有時剛告訴完,過一會她又問,我們以為她老人家糊塗了,但這個問題我們真的回答得出麼?
其四 對症下藥,不露痕跡
一次,我和一師兄商量買榴蓮給師父吃。買回後,她聽說師父不吃榴蓮,就留下給自己了。我得知後,把她罵了一頓,仍然把榴蓮拿給師父,但並沒有說罵人一節。師父很高興地收下了榴蓮,並給我講了一個故事:佛陀在世時,有人去出家,當時佛陀不在,佛陀的大弟子們用神通觀察這人三大阿僧祇劫都沒有出家的善根,於是就要把他趕走。佛陀正好回來,把這個人留下並答應他出家了。弟子們很不解,佛陀便告訴他們:你們只能看到三大阿僧祇劫,而三大阿僧祇之外,此人曾經念過一句阿彌陀佛,以此善根,成熟於今日。”當時我很納悶師父為啥給我講這個,等到明白後,便去向被我罵的那位師兄求忏悔了。
又一次,我又問師父:“最大的精進是什麼?”師父回答說是忍辱。當時我對這個答案頗感意外,也不太理解。後來才體會到,這正是對症下藥。事實上,我總是自以為很精進,而越“精進”越是貢高我慢,而這我慢,正像“家賊”一樣隱秘難防,時時遭其暗算。所以看好這個家賊,時時如水一樣把“我”放在最低,精進的同時不以為意,這才是真正的精進。
其五 愛國為基
有北京居士皈依師父,將名字、地址寫好給師父看後,師父還反復追問:“你是哪裡人啊?”那居士只得回答:“國籍是美國。”師父便說:“現在辦國籍很容易嘛,中國人還是自己國家的國籍好。”
其六 平常心是道
師父雖是一代高僧大德,宗門耆老,但她平時看上去,真的只是一位再尋常不過的老太太,半點“高僧”的味道都沒有。一次,有客人來,師父拿了幾塊錢讓當家師去買菜。但後來沒去買,師父便向當家師伸手道:“把錢還來。”直是“小氣如此”。平常幾乎每天都有很多信眾來看望親近她老人家。有的一來就拉家常,師父就陪他拉家常;有人喜歡聊政治,她老人家就跟你聊政治。有時候,我在身邊聽久了都覺得不耐煩,覺得來人太不知趣,拿這些廢話來浪費師父的時間。但師父和這些各式各樣的人都能聊得很起勁、很自在,真是“胡來胡現,漢來漢現”。而我卻在分別取捨裡真正浪費了時間。
其七 禅者風度
師父在建金山寺時,操勞過度,牙龈嚴重發炎,滿口牙齒都松動脫落了,且一直沒裝假牙,平常也就吃點霉豆腐和煮爛的青菜。加之住的也是一間不怎麼通風的小屋,這在很多人看來,無疑是艱苦樸素的美德,而師父只是無所謂罷了。她時常指著自己身體告訴我們“這只是一個假殼子”。當年師父在廣東海島做磚瓦時染上了嚴重的風濕病,腿經常痛。但每次師父說她腿痛的時候,我總覺得她是在說別人,因為你看不到她面上絲毫的難受。但出於孝心,我們一有機會就去給她老人家捏腿。
一居士給師父供養上好的天麻和川貝,並且仔細地跟師父講解東西的藥效。師父一直颔首聽著。後來,那居士才知道師父出生於中醫世家……
其八 聖凡之別
某年,一些剛受完式叉尼戒的學僧,當年就求受大戒,這是不如法的,但出乎我意外的是,師父竟然答應她們,還說:“這兩年我建安養院,沒錢拿給你們了。”當時很不解師父怎麼會“縱容”她們。後來讀到一個公案:xx居士家裡有塊石頭,想做成佛像,問xx禅師得否,師說:“得。”居士又說:“但那塊石頭曾經坐過踩過,怕不得吧?”於是師亦說:“不得。”原來聖人以百姓心為心,而如我凡夫只見到表面的對錯是非,哪裡知道更深的因緣。
其九 金山四得
凡是金山寺的常住,沒有誰不知道師父那經典的“四得”,因為師父對誰都要講這“四得”,不管你是新來的,還是老參上座;也不管你是個聰明的,還是傻的。每次只要師父一說“掐(吃,撫州方言)得苦”,我們就會接下去:“掐得虧,受得氣,放得下。”但這“四得”正是“三歲小兒說得到,八十老翁行不到”。
我曾聽說過師父的一則往事,這則往事正可以诠釋這“四得”:師父在某寺的時候,鄰住的鄉人在附近種了很多果樹,但果子總是被人偷吃,他們便懷疑是寺裡的出家人干的,而師父是新來的,於是成為第一懷疑對象。他們去問師父,師父只說“阿彌陀佛”。他們以為這是承認了,於是某某尼姑偷果子的消息很快傳開,那些果農看見師父就罵,師父也只是一句“阿彌陀佛”。於是,他們就給師父取了個外號叫“阿彌”。但知客師留心查訪,因為師父的平常為人怎麼看都不像個小偷。後來終於查出是另一個僧人干的,那些果農得知不是“阿彌”偷的,很後悔,更加敬佩“阿彌”的為人,提著果子去道歉,但師父也只是一句“阿彌陀佛”。
其十 苦口婆心
師父平日表堂,總是“老生常談”,總是那幾句反復說反復說的話,除了“四得”,還有“地獄門前僧道多”、“施主一粒米,大如須彌山,吃了不了道,披毛戴角還”、“要有慈悲心,要愛護小的,要關心老的”、“要愛國,要記住自己是中國人,不要有了錢就往國外跑”、“要冤親平等”、“要努力,不要光披著出家人衣服,不干出家人事”、“要發心做別人不願意做的事,要自知慚愧常行忏悔,好事莫與人爭”、“不能亂收徒弟,不能搞子孫廟,不能改叢林規矩”……這些話不但師父唠叨,古來的前輩祖師們也都這麼唠叨。就像虛雲老和尚每次開示都要說那句“不歷一番寒徹骨,哪得梅花撲鼻香”,師輩們如此,只為我們長不大啊!
其十一 空而不空
師父曾經自嘲:“印空印空,你一點不空,成天瞎操心,一天到晚打妄想。”聽得我心裡酸酸的,師父真的是“不為自己求安樂,但願眾生得離苦”。如若沒有這個“不空”,而沉空守寂,那就不是真正的“印空”了。